
▲人們渴望資訊,卻偏愛容易取得的資訊。(圖/達志/示意圖)
文/Michael Easter 譯/林慈敏
在現代的資訊深淵中,應該如何平衡我們的資訊消費者大腦呢?我二十歲出頭在《君子》(Esquire)雜誌實習時,被「大蒙蔽」狠狠打了一巴掌,取得資訊是多麼容易,而這又如何給了我們一幅現實的不完整圖像。那是二○一○年左右,一位資深編輯把我拉進會議室,教我如何找到更好的資訊。
那位編輯給了我一項奇特的報導任務,要去弄清楚教宗賺多少錢。其他兩名實習生和我一頭栽進了這項專案中,我們上網搜尋,也讀了一些報導,我甚至還採訪了一位大學的天主教學者與歷史學家。那位歷史學家支支吾吾地給了他們最好的估算。然後,我們把研究檔案用電子郵件傳給編輯,以便他把檔案轉交給一位寫手。
我們立刻收到了一封回信:「五分鐘後到會議室見我。」
那是一天的尾聲,編輯坐在一張長桌的首位,我們進入那間位於曼哈頓中城的玻璃牆會議室時,還能俯瞰第八大道的景色。我們都在一張椅子上坐下來,編輯久久說不出話來,然後重重地嘆了一口氣。「各位,不行,」他說。「不行,不行,不行。如果你們想知道教宗賺多少錢,就要打電話去該死的梵蒂岡問。」
「打電話去該死的梵蒂岡問。」+39-347-800-9066。自從那年以後,這句話就成了我腦海中的簡寫,提醒我該如何鍛鍊人類資訊消費者的肌肉。那是我們每次想深入了解某事的時候都應該考慮的一條經驗法則──不斷質疑資訊來源,以及只要有可能,永遠都要找到源頭。
哲學家阮教授解釋,知識與理解之間是有區別的,知識是掌握事實,理解則不同。「首先,」阮教授在二○二一年的一篇論文中寫道,「當我們理解某事,不僅掌握許多獨立的事實,還會看見那些事實是如何連結的……其次,當我們理解某事,就掌握了某些內部模型或對它的解釋,讓我們能用來做出預測、執行更進一步的調查,以及對新現象進行分類。」
當我們更努力地直接從源頭去獲得知識時,理解最有可能降臨。可以說是透過打電話去梵蒂岡來實現的,這需要更多的努力與更深入的探索。有意願去到那裡,拿起電話,或至少閱讀一份主要來源,例如一份研究報告,這會帶來更深入、更正確的理解。
想要知道某個東西的外觀或感覺如何?就去看或體驗它。對某人相信的事情感到好奇?就去問他們。在當下親自去做,能揭露更多訊息。
我們渴望資訊,卻偏愛容易取得的資訊。拿起電話或親自去見某人,會比待在螢幕後面閱讀其他人已經解讀的內容要來得更不確定、更無法預測與控制。這就符合了現象研究人員所稱的「線上大腦」。由哈佛醫學院(Harvard Medical School)、倫敦國王學院(King’s College London)與牛津大學等世界最菁英學術機構的科學家所組成的團隊,最近聚在一起研究線上大腦。他們說,網路已用三種方式改變了我們的大腦。
第一,傷害了我們專注的能力。這並不令人震驚,我們的工作和學習裝置與社交裝置相同,也與夢幻足球追蹤器相同,也與電視相同,也與……你知道重點在哪。利用匱乏循環的APP破壞了我們的注意力,並扼殺了深刻理解所需的專注力。
史丹佛大學的研究人員發現,人們在筆電上於不同的工作之間切換的頻率,高達每十九秒一次。超過一半的大學生承認,無法在不查看手機或不打開娛樂畫面的情況下用功念書十分鐘。
線上大腦的第二個影響是,我們已把一些記憶轉移至雲端。這有明顯的好處──像是我們口袋裡現在就有一部百科全書。但壞處是,這可能使我們更難將看似截然不同的資訊片段連結起來,彷彿我們無法取得填滿拼圖所需的碎片。拼圖的碎片不是全都倒出來放在桌上,反而是有些在一個房間,其他在另一個房間。
研究也支持這個概念。有個研究要求兩組人去尋找資訊,第一組人可以使用網路,第二組人則使用紙本百科全書。網路組更快找到資訊,這一點並不令人驚訝。但是任務完成後不久,跟那些使用紙本百科全書的人比較起來,他們正確回憶資訊的能力明顯較差。這份研究顯示,如果想要更記得住資訊,那麼比較費力地搜尋,像是找到對的書,然後在書中找到對的段落,可能是有利的。就像慢食比快食有利,慢資訊通常也比快資訊更好。
第三,科學家表示,網路正在改變社交互動。我們的大腦對線上與實體的社交互動反應似乎很類似,但有些研究顯示,網路的崛起造成年輕族群之間的社交焦慮,從二○○八年以來增加了三倍。研究人員指的是「一天二十四小時,一週七天的直接與間接媒體」,這或許是我的許多大學新聞系學生難以與消息來源接觸與談話的原因。當然,線上評論區似乎是可憎的人類行為總部。
史丹佛大學的研究人員報告,網路與其強烈影響人心的傾向無所不在,包括了日常社交、職業、智性與私人的生活。
我跟范德‧海談話時提到這個現象。他說:「在過去五年裡,每當我進行公開演講時,都有更多人問我,地球是不是平的。真的,有一陣子,我每一次去一間學校演說時,就會有一個人問我地球是不是平的,我不知道該如何回答。那讓我真正去思考,科學家努力去做的事情之一,是提出一個理論,然後設法去反駁它。因此我們特地去尋找與我們認為的現實互相矛盾的資訊,這就是我們確信自己取得一個可行理論的方式。如果無法找到任何反駁的方法,我們就會對它越來越適應,但仍然稱它為一個理論,因為在未來我們可能會學到更多東西。」
當我們看著不是平的地球時,范德‧海繼續說道:「我認為正在發生的是,我們可以取得太多資訊,它們可能是事實,也可能是不正確的。有問題時,我們傾向到網路上尋找只會強化我們已擁有觀念的資訊,你可以輕鬆找到那種強化的資訊,可能對任何想法變得更加堅定。」
阮教授解釋:發現我們所想的是正確的資訊感覺很棒。哲學家艾莉森‧高普尼克(Alison Gopnik)甚至稱它為「智性的高潮」(intellectual orgasm)。那是只有以思考維生的人才說得出來的話,但她抓住了重點。那個恍然大悟的「啊哈」時刻感覺很棒,就像中了頭獎。
另一方面,困惑是一種令人不適的提示,告訴我們要思考更多、搜尋更多資訊。當我們找到認為是正確的資訊,不適就會轉變為舒適,「啊哈!」我們驚呼。這帶來的清晰感不僅令人欣慰且感到值得,也告訴我們不用再去尋找更多資訊或思考更多。一旦有了一個「啊哈」時刻,我們就不需要另一個。可以把這想像成飢餓對上飽足,缺乏資訊就像是空腹,找到資訊就像吃完一個漢堡時滿足與幸福的狀態。
這種清晰的「啊哈」感受通常伴隨著真正理解某事而來,但並非總是如此。我們可能對一個主題感覺很清楚,同時又有一點錯了,甚至錯得很離譜。我們都經歷過這種事,次數多到我們不想承認。請記住第七章的內容,對一件事感覺九九%確定的人,有四○%的時候是錯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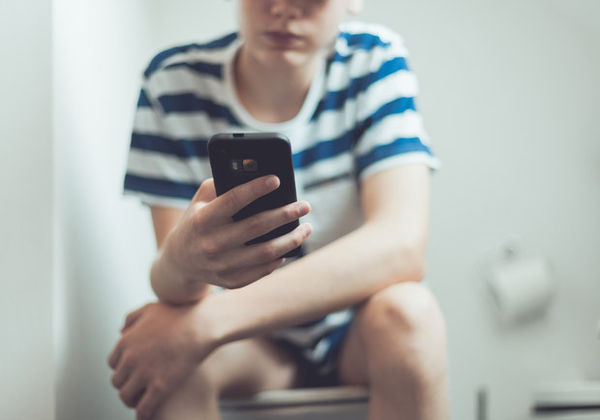
▲研究認為,網路已用三種方式改變大腦。(圖/翻攝自Unsplash)
還有很多地方很容易就看出我們錯在哪裡,例如,橋梁坍塌、牛排的堅韌度像皮革,或髮型使我們看起來像個怪人,我們就能看出有關如何造一座橋、煎一塊牛排或設計髮型的資訊是錯的,但是大多數的決策都是模糊的。
「我們是有限的存在,擁有受限的認知資源。」阮教授在一篇論文中寫道。「在日常生活中,我們必須弄清楚要做什麼:把錢花在哪裡、要投票給誰、支持哪位候選人。我們面對一連串持續的潛在相關資訊、證據與論點──遠遠超過我們能以任何決定性的方法評估的範圍。……要知道我們完全了解了某事,需要進行一次詳盡徹底的調查。」考慮到我們的世界有多麼複雜,這幾乎是不可能的事。
這可能與過去有所不同。對古老的祖先來說,「啊哈」的清晰感相當可靠,因為他們對資訊的追尋是直接的,要嘛找到食物,要嘛沒有;要嘛找到遮蔽處,要嘛沒找到;要嘛是地位崇高的領袖,要嘛不是。因此我們進化成相信「啊哈」的感覺,就是那種清晰的感覺。
但是目前在大多數情況下,我們不一定能選出最好的資訊。阮教授寫道,因此我們使用快速而寬鬆的「啊哈!」清晰感,來做出大略的估計,就是我們已做了足夠的思考並做出了好決定。但是這份「啊哈!」的感覺,在我們發現資訊中的缺陷之前,就停止進行搜尋。
例如,地平說陰謀論者馬克‧薩金特(Mark Sargent)跟《CNN》說他的觀點:「你感覺對人生與宇宙有了更好的掌控力,這感覺容易處理多了。」另一名地平說陰謀論者大衛‧魏斯(David Weiss)則說:「當你發現地球是平的……你會變得更能掌控自己的命運。」
大多數人不會相信地球是平的,但我們可能太常受到簡單資訊的影響,或者從網路上的愚蠢資訊中得到廉價、無意義的「啊哈」時刻,像是在家中是否應該脫鞋或是該如何懸掛藝術品。當我問阮教授,我們可以怎麼做,他把它拿來與食物做比較。
「如果你放棄考慮營養,要做出美味的食物很簡單。」他解釋道。「同樣的情況也發生在真相上:如果你不在乎真相與細微的差異,要提出吸引人的清晰概念也很簡單。」
他告訴我,我們應該質疑任何能快速輕易地帶來一種清晰感的資訊,那種「啊哈!」的感覺。我們應該利用那個感覺,當作尋找那個資訊可能是錯誤的一些細節的提示,就像打電話到梵蒂岡去問一樣,必須理性對待這一點,否則我們就會發瘋。但是,這對我們想了解的主題來說,是非常重要的。

本文摘自《大腦不滿足:打破「匱乏循環」,在數位浪潮中奪回生活主導權》/Michael Easter/方舟文化出版

讀者迴響